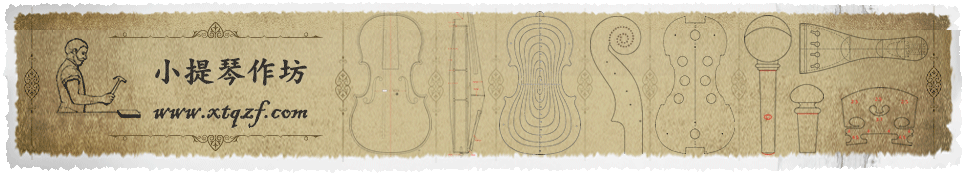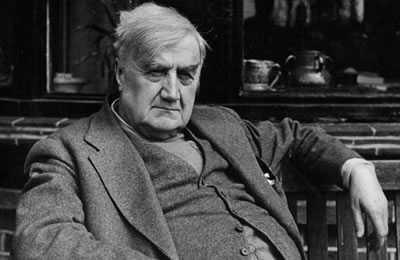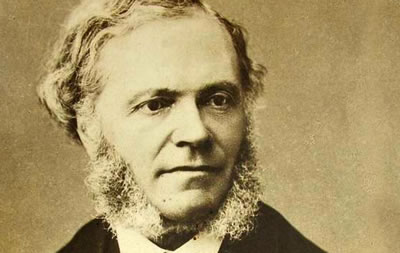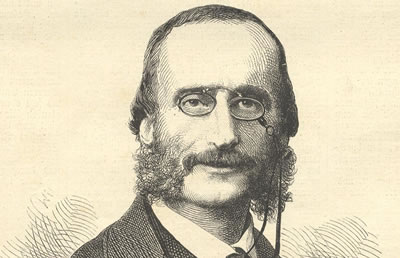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俄文:Пётр Иль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英文:Peter Ilynch Tchaikovsky,1840年5月7日-1893年11月6日))这位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作曲家于1840年5月7日(俄历4月25日)出生于在乌拉尔的佛根斯克。父亲是矿山工程师,在一所规模巨大的官办冶金工厂任厂长。柴可夫斯基的童年是在俄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优裕环境中度过的。十岁以前,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偏远的乌拉尔地区。这里流传着丰富的民间歌曲,特别是那种悠长、抒情的渔歌,更是经常在湖面上荡漾。这就是柴可夫斯基最早得到的难以忘怀的音乐印象。
1850 年,十岁的柴可夫斯基被送到圣彼得堡法律学校上学,这所寄宿的贵族子弟学校是专为司法部培养官吏的。在圣彼得堡他第一次观赏了葛令卡(M. Glinka, 1804-1857)的《伊万·苏萨宁》(Ivan Susanin,1833),从此对这部歌剧产生了终生不渝的爱。也是这时他才有更多的机会熟悉了俄国与外国作曲家的歌剧和交响乐作品。课余之暇,他学习钢琴,参加合唱,跟同学们一同奏乐自娱。1859 年在法律学校毕业后,柴可夫斯基到司法部任职,当上了一名九等文官。然而他对音乐的热爱却与日俱增。1861 年秋,他进入俄罗斯音乐协会附设圣彼得堡音乐班,开始业余学习作曲理论。 1862 年,音乐班改组成为俄国的第一所音乐学院-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柴可夫斯基被录取为首届的学生。他在1863年给妹妹的信中说:
去年我学了许多音乐理论,如今我坚信,迟早我是要献身于音乐的。你不要你不要以为我是幻想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我不过仅仅想从事我的才能吸引我的事情。当然,在我最终确信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官吏之前,我是不会彻底放弃公职的。
不过,对最终确信的思考很快就完成了,仅仅一个月后,即1863年5月,柴可夫斯基不顾父亲破产带来的经济威胁,不顾在沙俄社会以音乐为职业的渺茫前程,毅然辞去官职,投身音乐事业。他靠教授私人学生维持生计,从此走上了自由艺术加荆棘丛生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做一个靠自己能力谋生的艺术家。
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学院的老师是查伦巴(Nicolas Zaremba,1821-1879)和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 1830-1894)。由于他直至二十二岁才开始接受专业音乐教育,为了弥补失去的时光,他的学习是那样刻苦勤奋、专心致志,令他的老师也感到惊讶。他不仅钻研各门作曲理论,还学长笛和管风琴,参加学生乐队,尽可能的吸收一切可能获得的音乐知识和技能。1865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作品是用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的诗谱成大合唱曲《欢乐颂》(Ode to Joy)。
1866年,俄罗斯建立了第二所音乐学院-莫斯科音乐学院。就在这年的一月,柴可夫斯基接受尼古拉·鲁宾斯坦(Nicolay Rubinstein,
1835-1881)的邀请迁居莫斯科,成为该院第一位引人注目的年轻教授。于是在他的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即1866至1877年的莫斯科时期。
在莫斯科的这些年间,柴可夫斯基经常观赏莫斯科小剧院上演的现实主义戏剧表演,并和一些杰出的话剧演员深入交往。这不仅让他在歌剧创作原则方面得到帮助,也对他整个艺术观的确立都产生了影响。
在莫斯科,他也和列夫·托尔斯泰(L. N. Tolstoy, 1828-1910)有过接触。托尔斯泰在听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的慢板乐章《如歌似的行板》
(Andante Cantabile)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并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说:
我从不曾因自己的文学著作,而得到像您从这个奇妙的晚会所得到的如此珍贵的奖赏。我非常钟爱您的才华。
而柴可夫斯基对这位伟大文豪也是无限崇敬,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在古往今来的一切作家、艺术家中最伟大的就是托尔斯泰。只要有他一人,就足以使俄国人在别人述说欧洲给人类做出的一切伟大贡献时不至于低下头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柴可夫斯基在这些年里和俄国五人组(俄国五人组是1850-1860年代在俄国形成的一个以继承葛令卡传统,发展俄罗斯民族音乐创作为宗旨的作曲家团体。为首的是巴拉基雷夫(Mily Balakirev, 1837-1910),成员有鲍罗定(Alexander Borodin,1833-1887)、 库宜(Cesar Cui, 1835-1918)、 穆索斯基 (Modest Mussorgsky, 1839-1881)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Nikolai Rimsky-Korsakov, 1844-1908)。他们对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发 展居功至伟 。)的作曲家巴拉基雷夫以及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之间的友谊。巴拉基雷夫常向他提供标题音乐的创作题材。他们经常交换各自搜集的民歌,交流创作计画,切磋创作成果。柴可夫斯基以善意戏语把俄国五人组这个富于革新精神的创作团体称为「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雅各宾俱乐部原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民主派的组织,第三等级的代表。雅各宾人思想激进,行动激烈,1793年3、4月到1794年7月的雅各宾专政时期是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高潮时期。)。
其实,柴可夫斯基和俄国五人组的作曲家之间存在不少歧见。柴可夫斯基不赞同他们过于偏激的艺术观点,对他们彻底否定专业训练及学院派创作感动惊愕。俄国五人组则不满柴可夫斯基任教音乐学院,对他在创作中不仅采用农村歌曲,也采用城市小调作为素材大不以为然。尽管后来他们之间的分歧日渐扩大,各自走了不尽相同的艺术道路;但应该说,这一段友好交往使彼此都得益匪浅。柴可夫斯基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运用较多民歌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富有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音乐语言;他又透过这个时期创作标题交响曲音乐的实践,进一步掌握了运用音乐手段鲜明、准确刻画形象的本领,这些都和他与俄国五人组的相互交流有一定的关系。
柴可夫斯基的创作欲望十分强烈,对他来说创作是全部生活意义之所在,而对任何使创作中断的事情他都感到憎恨。在音乐学院授课已成为他的痛苦负担,但经济尚无保障以及对青年学子的责任感又使他不得不继续背负这教学重担。
这种难以忍受的精神重担终于导致精神疾病的爆发,加上一次只结合数周便告离异婚姻挫折,是他身心遭受沉重打击,几乎致他于死命。1877 年6月他在弟弟的陪同下旅居国外。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一位结识不久的友人-富孀梅克夫人(Nadezhda von Meck, 1831-1894)给予了他莫大的精神支持和物质帮助,使他逐渐度过了危机,也彻底摆脱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学工作。梅克夫人是个很有教养的音乐爱好者,像德彪西就曾担任过他的家庭乐师。她非常崇拜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则称她为能够洞悉我灵魂的朋友。他在信中对梅克夫人说:
如今从我的笔下流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献给您的!多亏了您,对工作的爱才以加倍的力量回到我的身上,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一分一秒永不会忘,是您给了我继续执行艺术家天职的可能。
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约定永不见面。有时,柴可夫斯基住在梅克夫人的庄园进行创作,而梅克夫人就住在比邻的另一庄园,两人虽然近在咫尺,却如相隔万里。他们的千言万语都是透过书信传递的。对柴可夫斯基来说,作曲是另一种、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宣泄方式。他认为作曲是心灵音乐的自白,能够按照自己的特性借助声音宣泄而出,就如同抒情诗人借助诗句倾诉情愫一般。
由于梅克夫人的精神支持和物质资助,柴可夫斯基终于有可能全力投身创作了。从1878年底至1885年,他有很多时间是在国外渡过的。义大利或瑞士的某个幽静的公寓往往成为他的栖身之所。然而,住在那些风光明媚、山水绮丽的地方,他也常常按耐不住强烈的乡愁。有时他返回俄国,借住在梅克夫人为他准备的美丽庄园,或住到乌克兰卡明卡(Kamenka)他妹妹的家里。他风尘仆仆、行踪不定,但那枝创作的笔却从未停息过。即便情绪十分恶劣,灵感似乎消逝的无影无踪的时候,他也总是强迫自己写。他认为灵感是一位不喜欢造访懒人的客人,无论何时都应该工作,一位真正诚实的艺术家是不能以兴致不佳为借口而不创作的。只要能够战胜自己的兴致不佳,灵感就会出现。
他的不朽杰作-歌剧《尤金·奥尼琴》(Eugene Onegin, 1877-1878)及第四交响曲(1877)就是这样写成的。而像小提琴协奏曲(1878)、《一八一二序曲》(Festival Overture, 1880)、弦乐小夜曲(1880)、《意大利随想曲》(1880)及钢琴三重奏《伟大艺术家的回忆》(1882)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名曲,也是在这些年从他的笔下源源不绝而出的。
八十年代中期,柴可夫斯基对于漫游的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于是从1885年起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乡间定居下来。但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的行程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更增加了。因为正是在1885年他正式作为指挥家登上舞台,在国内外开始了频繁密集的演出活动。在经济收入方面,他也完全可以无忧无虑了,除了稿酬,他还拥有梅克夫人的固定资助,而自1888年起,他又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取得年金3000卢布。
照理说,物质上、精神上他都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心情抑郁、心烦意乱、悲观绝望与无所适从的心情却是他的家常便饭。这样的心情由来已久,早在188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他就写道:
我无法瞒住自己。生活在乡间和孤独之中的一切诗情不知什么缘故实际上全都完了,只要一不工作,就苦闷并对未来感到恐惧、心神不定、忧郁、烦闷、有时甚至感到可怕。我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厌倦,一种忧郁的冷漠,就像不久我就会死一样,这种大限将至的感觉使我对自己生活中认为重要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毫无价值了。
柴可夫斯基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幸事件,如亲友相继亡故,无疑造人都在过成他巨大的心灵创伤,成为他精神危机的因素。除了种种个人生活的遭遇外,社会的原因无可否认也是应该加以探究的。柴可夫斯基敏感的天性在他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中鲜明的反映出来。住在乡间,他亲眼看到改革后农民的悲惨境遇。农民们从地主那里分得的土地都是一片光秃秃的沙砾,收入等于零,大多数人都在过苦日子。
农家的孩子命中注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要生活在永恒的黑暗和窒息中。他感到很难过,曾经出资为孩子们办了一所小学,但很快他就明白这是无济于事的。政治气氛也总是使他难以忍受。 1878 年时圣彼得堡的气氛是十分沉闷和压抑的,一方面是张惶失措的政府,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不幸的、疯狂的青年不经审讯便被流放到最贫脊的地方。柴可夫斯基认为能躲到艺术世界中去,不看这幅可悲情景的人是幸福的。
八十年代以后,柴可夫斯基更加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1882年他写道:
我们心爱的然而却是可悲的祖国处在最黑暗的时期,所有的人都感到莫名的不安,好像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行走,都感到时局不稳,但看不清前途。反动精神发展到如此程度,连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也当成革命宣传品来搜查。青年们在暴动,俄国的气氛实在很阴沉。
可见,令人窒息的社会空气他是深有所感的。
1893年10月28日(俄历10月16日)柴可夫斯基从莫斯科来到圣彼得堡指挥第六交响曲的首演,数日后据说他传染了霍乱。1893年11月6日(俄历 10月25日)凌晨三时,柴可夫斯基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圣彼得堡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送葬,他和葛令卡、穆索斯基、鲍罗定等俄罗斯伟大的音乐家们一起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公墓。
柴可夫斯基乐曲风格
综观柴可夫斯基的一生,他始终处于无所适从的矛盾彷徨中,而且越陷越深。一方面,他十分不满沙俄的黑暗现实,憎恨统治者的专横、暴力,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但同时,他也十分畏惧民意党人对统治者采取暴力行为,将其视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他挚爱着俄罗斯,每当逗留国外,他的心总被深沉的乡愁所煎熬;可是一返回祖国,他又大失所望,忍受不了社会空气的窒息,恨不得立刻离去。他敏锐的认识到国家的治理方式是”一切弱点、一切阴暗面”的根源,他思索过一些制度改革的问题;但又真诚的宣称自己是”皇朝的坚决拥护者”,认为沙皇制终归还是比西欧的民主制更好。
他极为珍视个人的自尊和人格,而在暗无天日的沙俄,他的自尊和人格却屡屡遭到践踏。他热切渴望获得个人幸福,幻想那个向他求婚的少女是塔姬雅娜般的理想化身,而实际上她却是个庸俗的小市民。
他不时为孤独所苦,但又对与人们交往感到憎恶。他经常被生死、善恶等他称之为命运的问题所困扰,不断到哲学著作及宗教里面去寻求答案,但却因未能找到答案而更加不知出路何在,更加茫然。
柴可夫斯基就是这样在重重矛盾和困惑中,希望和失望中,自信和自卑中,奋发和消沉中,辗转煎熬,并陷入痛苦、悲哀、绝望而不能自拔。他认为他生来就仿佛是专门为了和厄运进行争斗,寻求理想,追求永恒真理,却又永远达不到目的。
柴可夫斯基这种思想状态也正代表了那个时代俄国许多知识份子普遍的精神状态。这也正是他的创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惊心动魄的悲剧性的根源所在。这种悲剧性的特征在他六十年代的创作中已经初见端倪,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内容更复杂、更深刻了,表现形式更完美了。他在音乐创作里,特别是交响音乐创作里,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视为美好的一切理想化,赋予它最优美、真挚、深情、感人的音乐形象;同时又把达到理想中的阻碍,造成他心灵的痛苦,使他感到惶恐而又无法理解的种种复杂而矛盾的因素,这两种对立的悲剧性冲突成为他许多作品构思的基础。
柴可夫斯基的另一个突出的创作特征,就是真实的表现他个人的亲身感受。他不像俄国五人组的作曲家那样喜好取材于民间的史诗、传说、神话以及人民与统治者斗争的历史;他所追求的创作题材是建立在他所经历的或看到过的、能使他感动的情结和冲突上的。因此他的音乐不像俄国五人组的音乐那样偏重客观描写性,而是强调主观抒情性。特别是交响乐,他更视之为单纯为抒情的过程、来自心灵的独白。他的音乐总是发自内心深处、热忱、真挚、感人肺腑,充满感人的抒情性,同时又结合着强烈、震撼人心的戏剧性。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个人风格非常突出。这一点最鲜明的表现在他的旋律中。旋律是他创作的首要因素,也是他音乐中的灵魂。他富有个性的旋律风格是植根于俄罗斯民族民间音乐的土壤中的。对柴可夫斯基的旋律语言发生影响的主要不是农民歌曲,而是流传于俄罗斯城市中的小调和浪漫曲。他常常在自己写作的时候直接采用某个他喜爱的民歌进行加工,他的音乐具有俄罗斯因素,也就是采用了与民歌有关系的旋律、和声手法,那是因为他生长于偏僻的内地,自幼就领略到俄罗斯民歌难以言传、富于特色的美,那也是因为他热爱俄罗斯因素的一切表现,简而言之,因为柴可夫斯基是一位道道地地的俄罗斯人。
一般来说,直接以民歌为主题,只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次要方面;他认为民歌只是在创作时所用的种籽,艺术家要像园丁那样善于掌握适当的土壤、时令、气候,以培育出自己的芳香美丽的花朵。
柴可夫斯基还总是在自己的创作中把深刻与通俗性紧密结合起来,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成为大众的财产。他竭尽全部心力,热切渴望他的音乐广为人知,希望爱它并从中获得安慰和支持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他的作品是俄国作曲家中最受青睐的一个。
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莫斯科时期及成熟期。早在1864年就读于音乐学院的时候,他便采用自己最喜爱的俄罗斯戏剧-奥斯特罗夫斯基(N. Ostrovsky)的《大雷雨》(The storm)写作了一首管弦乐序曲。话剧《大雷雨》在1859年的上演曾是震动俄国社会的一件大事,因为他尖锐的提出了俄国妇女在宗法制家庭中受到残酷的压迫及奴役,要求冲破牢笼、争取解放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这出悲剧反映了俄国女性的人格感和自尊感的觉醒,反映了他们挣脱荒诞无稽的中世纪束缚的愿望。柴可夫斯基不顾老师的反对而选取《大雷雨》作为创作题材,表明了他对沙俄社会这个「黑暗王国」的态度,反映了他六十年代的思想倾向。而这种思想倾向在幻想序曲《罗密欧与茱丽叶》中得到了更加完美的艺术体现。
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时期(1866-1877)的创作大多是反映俄罗斯生活的,只有少数采用别国题材。与他以后的作品不同,这些作品常常直接以俄罗斯或乌克兰的民歌曲调为主题。总而言之,柴可夫斯基这时对民歌的兴趣比较浓厚,他在 1868 到 1869 年为钢琴四手联弹改编的五十首民歌也表明了这一点。
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有着较多明朗、乐观的特质,第一钢琴协奏曲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代表。还有一些作品是对民间生活的鲜明描述,生动的表达了乡民的幽默和风趣、但也有刻画另一种情绪的作品,例如:表现对封建桎梏的抗议,对理想境界的渴望,渗透着悲歌式的情调,甚至具有悲剧性的效果,《罗密欧与茱丽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柴可夫斯基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非常多样,甚至互相矛盾,这样的现象并非凭空而来,它是俄国特定阶层的知识份子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感受在艺术上的反映。
在莫斯科时期,柴可夫斯基创作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作品。其中包括歌剧《地方官》(The Tangle, 1868)、《仙女》(Undine, 1869)、《奥普利其尼克》(The Oprichnik, 1872)、《铁匠瓦库拉》(Kuznets Vakula,1875)、芭蕾舞剧《天鹅湖》(Swan Lake, 1876),第一交响曲《冬之梦》(Winter Dreams, 1866)、第二交响曲《小俄罗斯》(Little Russian, 1872)、第三交响曲《波兰》(Polish, 1875)、第一号降 B 小调钢琴协奏曲(1875)、大提琴协奏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钢琴小品套曲《四季》(Les Saisons,1876),以及其他许多器乐曲和声乐浪漫曲。
第四交响曲和歌剧《尤琴·奥尼金》也是在莫斯科动手写作的,但这两部作品是跨时期的创作,他们揭开了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新的一页,标志着他创作成熟期的开始。
1878-1893 年是柴可夫斯基的成熟期,他在这个阶段的创作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像《曼弗列德》交响曲(Manfred, 1885)、第五交响曲(1888)、第六交响曲《悲怆》(Pathetique, 1893)、幻想序曲《罗密欧与茱丽叶》(Romeo and Juliet, 1880)、芭蕾舞剧《睡美人》(The Sleeping Beauty, 1889)及胡桃钳等等这样一些杰出的作品就属于他晚期的代表作。
此时柴可夫斯基已是俄国首屈一指的大作曲家了,他受到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作品不仅在俄国,在欧美也开始大量上演,柴可夫斯基也数度以作曲家和指挥家的双重身份到欧洲和北美进行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1890 年他的芭蕾舞剧《睡美人》在圣彼得堡首演,同年歌剧《黑桃皇后》亦于圣彼得堡及基辅首演,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也为他从事音乐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1891年他应邀为荣誉贵宾出席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开幕典礼,并在巴黎、纽约及费城等地指挥自己的作品演出,获得成功,《黑桃皇后》也在莫斯科首演。1892 年他的歌剧《尤金·奥尼琴》由马勒指挥在汉堡首演,同年他当选了巴黎优雅艺术研究院通讯院士,且歌剧《约兰塔》(Iolanthe, 1891)、芭蕾舞剧《胡桃钳》亦于圣彼得堡首演。1893年他在伦敦指挥第四交响曲演出,并当选剑桥大学荣誉博士,而第六交响曲也在圣彼得堡首演。
那时侨居西欧的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 1818-1883)给列夫·托尔斯泰写的一封信有这样的内容:
柴可夫斯基的名气在此地已经大为提高。在德国,他早已引人注目,在剑桥,一位英国音乐教授对我说,柴可夫斯基是当代乐坛最杰出的人物。
波西米亚作曲家德沃夏克(A.Dvorak, 1841-1904)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对他的歌剧《尤金·奥尼琴》表示衷心的欣赏:
你这部歌剧给了我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这部美丽的作品,他的热情是如此丰富,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出技巧的精湛;总之,这是召唤我们,深深感动我们,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音乐。
由此可见,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风格已获得广泛的尊敬和爱戴。